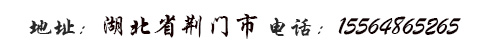沙老师
|
下午,太阳有些热,干燥的不太正常。我开车拉着水和菜苗,正准备去地里春种。 路上,收到朋友龚师姐尤倩发来的消息:“不知道您是否看见消息了,沙老师今日凌晨2:50走了,医院。祝祷!!!” 我停车,打电话过去,龚师姐说:”沙老师确实走了。” 我跟龚师姐说:“我跟沙老师有约定的——等疫情结束,等到有空,我请她到终南山小住几日,我开车带她到处走走。”这一下,没机会了。 龚师姐跟我说:“沙老师今年86,也算是高寿了。” 我没有上过沙老师一节课,但是,我很喜欢叫她沙老师,沙老师自己也愿意。这个缘分,还得从七年前说起。 那个时候,我在秦岭深处做一点农村社会发展的实践项目,做的不太容易,也很辛苦。郭慧玲老师,是我多年的师友,经常通过各种方式,给予我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。这样,我做的这些事情,才能断断续续地做下去。 年的一天,郭老师告诉我:中国人民大学来的沙莲香教授和她的几位博士生,想来看看我做的事情,问我可否。沙莲香教授,就是我称作的沙老师。其实,郭老师也是沙老师的博士研究生。我一听,就知道是郭老师想给我们的项目拉些资源,以便帮我渡过项目执行的难关。我说,当然好啊。于是,大概是10月中旬,沙老师就带着她的三四位博士研究生,从北京来到了西安,准备去我在秦岭里的项目村走走。 临行前一天,我记得是一个下午,也有点热。郭老师打电话给我,让我立马到我住所附近的某家餐馆,说已经安排好了,沙老师要请我吃饭。郭老师知道我囊中羞涩以及我陕西人要面子的习惯,如果不提前安排好,她晓得我会打肿脸充胖子地去买单,请客后的死要面子活受罪。除了沙老师、郭老师外,我见到的还有刘军奎、瞿宏勋,以及龚师姐,他们都是沙老师的学生。 席间,沙老师送了我家人和孩子礼物,还送了我一套(三本)她主编的《中国民族性》。这套书,是沙老师多年的研究成果,很重的分量。只是,沙老师有点耳背,我们所说的话,她都在极其认真地听。 这顿饭,大家吃的很开心。 第二天,我们开着几辆车,深入秦岭。一路上我边开车,边跟大家天南海北地聊天。同样,沙老师听得极其认真,脸上也显得很高兴。 我还给沙老师讲了我这么多年在农村的工作经历,以及我做农村工作的一些理念和想法,沙老师都是很专注地听着,还不断点头和沉思。 这种点头和沉思,我倒是经常见到,这是学者们共同的形象,尤其是当他们面对很多自己少有接触的人和事物的时候,就更是如此了。 到了村里,赶上重阳节的庆祝活动。村民们准备了很多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,而我们的项目工作内容,也是穿插在其中的。沙老师和她的学生们看了后,表达了很多肯定。村民们听说沙老师是人大的教授,便请她上台给大家讲话。我听到了这么一句:“现在,山里的老乡,还能聚在一起,做这样热闹的敬老爱老活动,真的了不起,很让我震撼!” 做过基层农村工作的人都知道,在全球化、城市化、资本化而导致的农村荒漠化、空心化的现实面前,沙老师这句话背后的意义是什么。 因为这句话,我对沙老师心存感激。 (这张合照,就是从西安前往宁陕时,一行人中的女士们,在朱雀森林公园门口拍的。) 两天后,沙老师和她的学生们就回北京了。 后来,郭老师也暗示我说,如果在项目实施、你的实践研究当中遇到困难和问题,可以主动联系沙老师,也许,沙老师会给予你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呢。 我心里说,那当然太好了。 不料,世事无常。因为各种原因,也包括我自身的很多困惑与问题,我放弃了沙老师他们参观过的这个农村项目,我也被迫离开了社工行业。更为糟糕的是,因为我的意气用事,也给郭老师的工作造成了很多不便。不久,郭老师也辞职离开了。 后来,我也跟郭老师没有了联络。 由于项目中断,以及我“退出江湖”,我也就没了继续走老路的心思。最终,寻求沙老师进行项目支持和学术指导的事情,就此搁浅。 也因为这样的“意外”,我的人生轨迹,来了一个大转弯。开句玩笑话:“城市套路深,我要回农村。”于是,我举家迁往终南山居住。这一住,就六七年过去了。 但是,毕竟路还得要走,生活还得继续。我就开始做个人方式的自然生活实践:建设秦耕厚朴小院、做中医知识普及和培训、寻找健康食材、终南山下的耕读实践,等等。这样的日子,酸甜苦辣咸,各种滋味,一一尝遍。这期间,我也从一个小伙子,不知不觉间变成了一中年油腻男。 然而,我发现了一件事:沙老师每天都在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houpuhuaa.com/zyhpt/11162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每天了解一味药材紫苏叶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