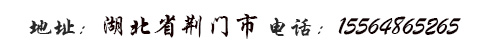杨俊国常州日报发草说
|
有我写作直抒胸臆不事雕琢神韵灵趣 杨俊国:东亚汉学学会会员,常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。 草说 □杨俊国 草是上帝用来给世界打底的植物。 极少数的草获得了人类的青睐,入住人类的家园,享受高贵的待遇。譬如兰、菊、荷、菖蒲、水仙等等,被赋予高洁的品性,喜之者甚多,譬如那个楚国的三闾大夫。“纫秋兰以为佩”,屈子是不是真的把它佩挂在身上?不知道,但他喜欢香草竟至成癖,也许他觉得自己就是一株芳草。每年端午,老百姓郑重地把一种植物插在门楣上,有特殊的馨香,那叫艾草。 绝大多数草,没有这样的命运。除非植物学家,人们甚至叫不出它们的名字。即便有名字,在民间也是一个俗名,比如毛毛草、蛐蛐草、狗尾巴草之类。《诗经》里的“芣苡”,学名“车前子”,在乡下就叫“猪耳朵草”,如山里的娃叫石头叫狗蛋。它们是一个集体名词,笼而统之,名之曰“草”。按照上苍设置的遗传密码,它们走完自己的一生。春天,绽出新绿,然后快活一个夏天,秋天时寸草结籽,冬日便藏根于大地。一荣一枯,四季轮回。 地球上的第一株草从哪里来?没有人知道。科学家在阿曼的一个洞穴里采集到植物种子化石,这让我们知道,至少在奥陶纪,也就是在距今4亿到5亿年前的时候,地球上可能就有了陆生植物。年,我国科学家发现1.64亿年前侏罗纪地层中的一种草本植物化石。化石是神的作品,植物或动物偶然落入沉积泥沙中被掩埋,几千万年甚至几亿年,沉积物成为石头,它们的身姿便留存至今,古老的灵魂定格在岩石上。 庄稼也曾是草。在漫长的渔猎时代,获取食物并非一件易事。饥肠辘辘时,便会采摘草木果实或挖掘植物根茎来果腹。人们发现了一种草籽,嗯,能吃哩!于是,一些种子落在土地上,不是风吹来的,也不是鸟带来的,而是一位先民撒在窝棚旁的土壤里。第二年长出新的植株,结出果实。于是,一个新时代来临,迁徙逐渐变为定居,人类的家园文化开始了。毋庸置疑,所有的农作物起初都是野生杂草,小麦、大麦、燕麦、豌豆等等,无一例外。在浙江上山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距今1万年之前人类食用大米的痕迹,那时候,稗草中的一支已经被“驯化”为水稻。 草是上苍的厚赐。无法设想一个没有草的世界。 北方苦寒之地,西部沙漠戈壁,但凡有一点土地的气息,就会有它们的身影。风把它们的种子刮到哪儿,鸟把它们屙到哪儿,如果幸运落在土里,哪怕是一个石缝,就在那里扎下根,活下来,久而久之,繁衍出一个家族。于是,草总是与底层百姓相关,谓之“草民”。草民对草,甚至比植物学家知道得还多。盖草房,织草甸,编草帽,打草鞋,做蓑衣,放牛喂猪,草几乎伴随着他们生活。我下乡插队时,村里一个婶婶,似乎什么草都认识,每年二三月,便会上山挖回各种野菜,与红薯、玉米和豌豆调配,度过青黄不接的日子。 每一种草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基因。蒲公英亭亭玉立,泥糊菜贴在地上如几何图案,马齿苋叶厚如绿玉,鹅儿肠自由行走,苍老的野灰菜壮如一棵草树。每种草都开出属于自己的花。陕南民谚:“萝卜地里刺叶花,人家不夸自己夸。”我曾看见过大片的荠菜,白色的荠菜花如满坡的蝴蝶。我也曾在路边看到过一株杂草,开满花,紫红色,碎如米粒。在上帝眼里,它与牡丹同等高贵。知堂先生《故乡的野菜》中的紫云英,在我生活过的陕南叫苕子,是用来沤肥的植物,在他笔下如此诗意盎然,读完竟引起如烟的回忆。 草虽卑微,却生性自由。也许,这就是许多文人喜欢它的原因。西晋有个嵇含,“竹林七贤”之一嵇康的侄孙。他崇庄子,喜草木,每至一地辄悉心记录奇花异草,给后世留下一本《南方草木状》,比西方的植物学专著要早多年。厚朴的灵魂往往具有植物属性。文人墨客喜欢用草给自己的住所命名,例如孔明的“诸葛草庐”、杜甫的“浣花草堂”、白居易的“庐山草堂”、纪晓岚的“阅微草堂”等等。卑微之草,此时一变而为风雅之物。 北宋有个诗人叫杨朴,活得散淡,常独自骑着驴出行,“每欲作诗,即伏草中冥搜,或得句,则跃而出,遇之者皆惊。”忽得妙句一跃而起,每每把路人吓得半死,此种构思诗歌的过程十分另类。“就客饮时担酒去,见鱼游处拨萍开”,也许就是从草里飞出的诗句。我也曾卧在草丛里,诗未觅得,却看到一个男孩儿,他编织了一个草冠,认真地戴在姑娘的头上,然后挥手告别。画外,蔓草尽头,信天游的曲调响起:“天上的雀雀儿地下的草,哥哥哟莫把妹忘了!” 这支歌,你肯定没听过,是我虚构的,因草而来。 ……终南山下有田园…… 投稿加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houpuhuaa.com/hpttp/11157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日本盆景的气质在哪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